今年是畅销小说《尘埃落定》获得茅盾文学奖25周年。从最年轻的茅奖获得者,到如今有超过40年创作经历的知名作家,萦绕阿来的不是沾沾自喜,而是日渐老去带来的关于生命短促的感慨。好在,他一直在行走,一直在阅读和书写。
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回望自己的创作生涯,阿来发现,多年的创作、探索、想象,让他越来越接近世界真实的那一部分。

作家中的植物学家
阿来早年有初步写作冲动时,两位诗人是他的偶像,一位是美国诗人惠特曼,一位是拉美诗人聂鲁达,两位都是在广阔大地上穿越行走的书写者。大地行走式写作,大地行走式阅读,贯穿阿来的创作生涯。
年逾60的阿来,一直在行走中写作,他在一个固定地点不超过一个月,超过一个月就要到大荒大野中去,到雪山峡谷中去。“我垂首坐在山顶,河流轰鸣,道路回转,山如波涛。我在倾听,听到人类过去、现在、未来,关于亘古的语言。”这种写作方式,过程本身非常美妙,阿来非常喜欢。
20世纪90年代,阿来走遍5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区,调查走访了18家土司的历史现场和文化史料,在不断了解土司制度兴衰中,自然而然沉淀出长篇小说《尘埃落定》。
近年来,黄河源头、西南高地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成为阿来的写作对象,他在四川阿坝、甘孜、凉山以及西藏、云南、贵州等地广阔的雪山、峡谷行走,写出《去有风的旷野》《西高地行记》《大河源》等散文集。
在稻城亚丁,公路消失了,只有古老的岩石,阿来抚摸百万岁的石头,想象一朵花的凋零,感受地老天荒;在十二背后,他借由喀斯特溶洞遥想岩石的几亿年历史,思考聂鲁达的诗句“石头之内有石头,人在哪里”;在皮洛,他吃饱了蘑菇,感觉自己变成了一棵充满香气的树;在四姑娘山,他感受杜甫“雪岭界天白”的意境;在米仓山,他像诗人元稹一样相逢了“轻红”的杜鹃花……阿来将行走中的奇遇和感受写到散文中。
他走过巴颜喀拉山脉等地,写下黄河源头的地理特征、壮丽景色,也写下雪莲花、绿绒蒿、鼠兔等自然界的动植物,为黄河源立传。
阿来对青藏高原的形成、黄河源的水系、动植物的科属、海拔与温度变化等如数家珍,进行了系统的学习、观察和研究。阿来之前的作品偏重人文,但今天的社会有很多问题,只是就人文说人文恐怕是不行的,他想让自己的创作有一个时空性转换,用偏科学观的写作去关注地理、气象、水文、土地上生长的各种生命体。对于为黄河源立传,阿来称,从古至今我们对黄河的认识和书写,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及汉文化发展中,对大河的上游几乎一无所知,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才确定了黄河源头,知道黄河从何而来,但黄河源多样化生物的生存是什么样的,缺少科学性的文学书写。
阿来笃信无论写作还是阅读,行走与书都互相映照,路是书的延伸,书又是路的升华。“作家去采风,应该像一个人类学家、生物学家、地理学家去工作、去调查。经过这个过程,写作者对山川、人文的感受,就不完全是想象的。依赖实际体验的想象非常坚实,不会是喧哗的、病态空虚的。病态空虚的文学想象,会掏空、削弱文学本质应该具有的情感和认知的力量。”
评论界看到了阿来写作的不断转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认为,阿来拥有的世界,是大部分中国作家或全世界作家都不可能拥有的,他所见的风光是世界上最高的风光,他走的路是非常辽阔的路,他写出了在汉语书写里未被广泛关注的名词,比如花椒树、紫菀、甘松以及各种蕨类植物,这些汉语世界中少见的词语,在他那里成为常用语,给它们一种文学的光泽。“阿来的作品植物充实丰饶,文学世界变得斑驳灿烂,他成为一个博物学者、博物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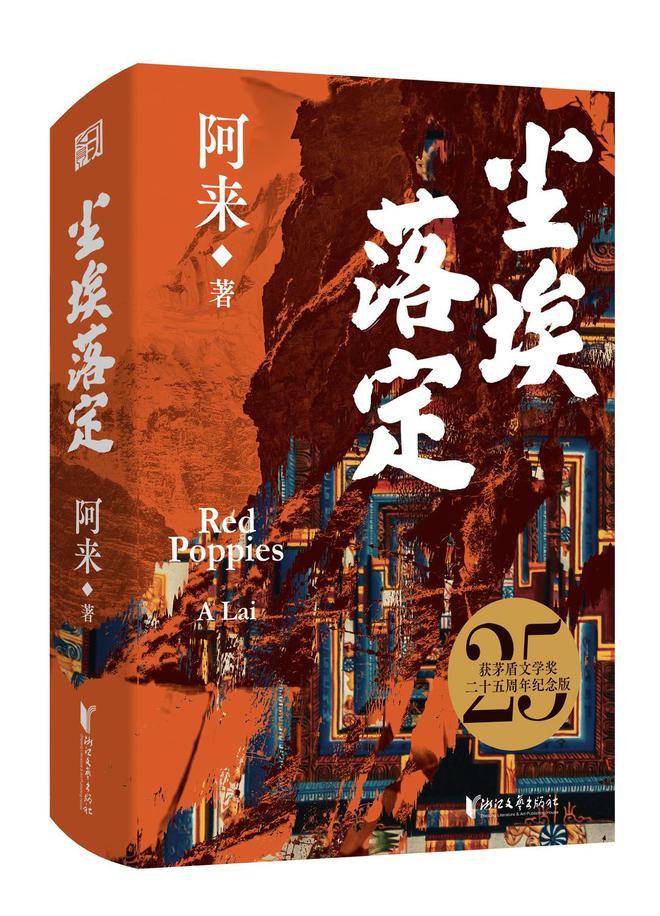
“没有这样的书,我来写一本”
“我出生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小村子,只有20户人家。但这个村子又很大,每户之间的距离都很远。穿过我老家那条狭窄的公路,我去最近的舅舅家要走20多公里。村子有森林、雪山、草场、庄稼地。”阿来这样描述他的家乡四川省阿坝州马塘村,这里有梭磨河、鹧鸪山,有独特的嘉绒藏族人文风景。
阿来6岁上学开始学汉语,小学到初中在边上学边砍柴、捡菌子中度过。初中毕业后,他继续务农,家乡修水电站招民工,他在工地挖土方、抬石头,后来因为有文化,被挑中当了一名拖拉机手。阿来小时候以为自己会和别人一样,种青稞,放羊,娶妻,生子,在偏远的小山寨安安静静地过一辈子。很快高考恢复,18岁的阿来下了夜班,赶了半夜山路,穿着开拖拉机的工地服,走进考场。他没能考上自己喜欢的地质专业,而是去了马尔康师范学校,后来在家乡当老师,热衷阅读的他,有了写作的冲动。
阿来看到,家乡的世界又大又小,人们很质朴,也很保守,他们很热爱乡土,但热爱到另一种程度,会变成固执的冥顽不灵。他想通过文学开启对自己的建构和解放,从文学中知道另外的世界,从写作中更深入地理解世界,认为写作的最终诉求是有关于人的建构。
他最先开始写诗歌,出版了诗歌集《梭磨河》,后来又出版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成为作家后,家乡不仅成为阿来小说故事的地理场域,对家乡人文历史的反复思考和书写,也构建了其写作的脉络走向、核心追求,那就是“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
在《尘埃落定》的开头,“我”在一个下雪的早晨,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小说的结尾,血滴在地板上,“我”在床上变冷时,血也慢慢地在地板上变成了黑夜的颜色……小说以傻子少爷离奇人生的尘埃落定为主线,呈现了20世纪上半叶藏族土司制度的崩溃中,一个大家族内部的复杂纠葛,一个个鲜活的男男女女的命运。因为写了不一样的藏族故事,开辟了新的文学地标,这部小说不属于先锋的、现代的、寻根的或伤痕的任何流派,与当时文学潮不合流,无法被定义、被归类,造就了它多舛的命运。被多家出版社拒绝后,书稿历经4年,终于在1998年与读者见面。
回望这部作品的写作,阿来说,30岁时觉得写作如果只为名和利,是非常虚伪的,他突然就写不动了,暂停了写作。34岁又重新拿起笔,思考如何写作,写的就是《尘埃落定》。“这中间几年,想要建构一个人,但突然发现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们从小读中国史,读世界史,都是大事情,法国大革命、鸦片战争……我们村、我们乡、我们县呢?我发现中国人缺少一种实在的,跟自己相关的历史观。那怎么解决呢?书店里没有这些书,我来写一本,以本乡本土为历史。《尘埃落定》就基于这样一个想法产生。”
《尘埃落定》更打动读者的是一个个人在历史变革中的权欲、纠葛和悲痛,描绘的不仅仅是土司制度的崩溃,而是历史的问题、人的生存问题。阿来曾表示,他不希望仅仅把这部小说看成是藏族的历史故事,因为从人本身、人类所有的共通性来讲,文化的差异、生活的差异是小的,在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情感状态当中,共通性要大于差异性,或者是普遍性大于特殊性。“文学不是寻找差异性的,而是在差异性当中寻找全人类的共通性、文化价值。”
阿来说,小说出版后踏上了自己的命运之旅,对将来的际遇已经无能为力。“一个人有自己的命运,一本书也一样。它走向世界,流布于人群中的故事不再由作家操控把握,而是很多人、很多社会因素参与进来,共同创造着。”《尘埃落定》出版后引发文学圈的关注和讨论,斩获2000年茅盾文学奖,阿来成为该奖最年轻的获得者。后经过影视化、舞台剧改编等,这部小说迅速大众化,成为纯文学中难得的既经典又有市场的作品。自出版以来,这部小说畅销已逾500万册,证明了当代文学在如今成为经典的可能性。
阿来在不同场合被多次问及《尘埃落定》为什么畅销,他自我分析,这部小说有点规律,它的语言方式和某种抒情性是很特别的,语言的节奏感较好;它还抵达了对人性、对历史真相的一些基本认知。“不过,它绝对不是那种一上来就说‘注意啊,老子要讲一个深刻道理’的小说。”

“人”的写作
《尘埃落定》写的是20世纪前50年发生的故事,阿来顺着这样的时间脉络,又以故乡的村子为背景,陆续创作以《空山》为代表的《机村史诗》六部曲,写新中国成立后藏族山村50年的编年史。
旧制度解体后,机村被纳入崭新的社会体制,机村人世世代代坚守的一些传统被颠覆;因乱砍滥伐,机村土地被毁,伐木工人与农民间的矛盾一触即发;倒卖木材的年轻人最终身陷囹圄;酒吧、游乐项目等现代事物“入侵”机村,考古队发掘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村庄遗迹,机村成了博物馆,人被迁移……6个故事,几十个主要人物的命运在这个村子展开,“机村人这几十年所经历的变迁,可能已经超过了过去的一千年。”
通过《机村史诗》六部曲,阿来想探讨的是“新的东西来了,新的东西如何生长”。“摧枯拉朽非常容易,把一座旧房子推翻非常容易,但要建一座比老房子更好的房子是相当不容易的。今天,在很多文化建构上破坏了旧的,但替代旧的那个新的东西未必超过旧的。制度性的创新,一张纸就宣布了,但真正把人改变是很难的。”阿来开始思考,文化要变,往好处变,往新处变,为何如此之难,是不是有更深层的原因。他开始研究史诗,写出重述神话故事的长篇小说《格萨尔王》,去回答自己的疑问。
书写地震灾难的长篇小说《云中记》,探讨的是关于人和自然、生存和死亡的人生终极命题。地震后很多乡镇村庄劫后重生,也有城镇村庄与许多人彻底消失,阿来想写这种消失,不只是沉湎于凄凉的悲悼,而是要写出生命的庄严,写出人类精神的伟大。
评论家谢有顺说,作为一个藏族人,阿来想祛魅一种被神秘化、浪漫化了的西藏,这是他的责任,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在祛魅过程中,阿来主要想写人的普遍性、共同性,消除分别心,写他所熟悉的人群也像普通人一样过着平凡普通的生活,在作品中突出“人”这个主题。“阿来在历史和自然中理解人,真正打动他的是在这块土地上渺小而坚韧活着的那些人,是一张张难以忘记的面孔,这就构成了人类前行的核心的东西,这种对人的理解是人文性的。阿来重新理解了世俗中的人,也重新理解了生生不息的生活,不可摧毁的意志,不可撼动的精神。这一点让阿来区别于很多作家,可能也是他对文学一个极大的贡献。”
阿来不止一次说过“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他的写作聚焦人,同时通过写作进行着自我建构。相比通过写作去影响别人,他想通过写作重构自己。“某种文化的影响下,一个人可能忠爱、忠诚,也可能偏激、狭隘,没有超越性。既基于一种文化,同时又超越这种文化;既基于个人生存,同时其对社会的理解又超越生存的基本原则,我就是在这样的道路上奔走着。”阿来建构自己的过程痛苦又愉悦,形诸笔墨后会在别人身上引起同感,找到的这些人就是自己最好的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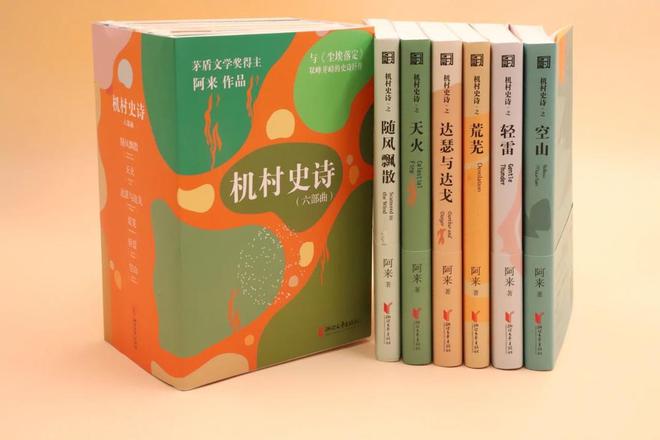
路径靠自己找
作家毕飞宇有一个有趣的观点:如果说6岁之前的语言叫母语,6岁之后所学的语言叫非母语,那么阿来一直在用非母语写作,“非常了不起。”毕飞宇发现,虽然《尘埃落定》如此伟大、如此重要,作为小说家的阿来,其汉语水平在50岁之后依然在提升,很了不得。
历经40多年,阿来的创作也一直在转向和突破,从诗歌、小说、剧作、散文,再到长篇非虚构等文体,逐一探索,不断写出不一样的东西。阿来的诗歌写作其实很短暂,刚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还是一个年轻人时,写作的抒情性更强烈一些,才去写诗歌,但30岁以后再没有写过诗。后来的写作,他想虚构一点,就用小说的方式;想表达真实的境况,就用散文或者非虚构写作。“写作中,是内容决定形式,而非形式决定内容,所以作家在写作中要看哪种体裁表达更有利。体裁一点不重要,不论是诗歌、散文、小说,还是纪实文学,关心的都是人、社会以及更大的自然世界。”
阿来拥有的世界是独特的。有人认为,阿来出生在一个未被作家文笔开垦过的地方,有着写作上的天然优势。从历史到人文,再到山川自然,在审视这种聚焦广阔天地和时空的书写时,阿来告诉记者,历史上的复兴地带,也就是中原,历史非常漫长,有它的文化、教育、文学等,几乎没有哪一个地方没有被诗人、作家的文笔大量地写过,形成了现成的经验和路径,这种写作的好处是写起来有据可依,有套路往下走,坏处是别人都写过了,再去写困难和挑战比较大。“我的家乡在历史上处在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地方,在我之前,那里不是没有人写过,但至少是没有人成功地写过。而我的写作很多时候是要去开天辟地的。写未被写过的地方挑战也很大,不知道怎么写,没有经验可以参考。”
阿来认为,做第一个作家,用文字去重新创造这个未被书写的地方,全靠自己去找路径,有的人没找到路径,失去了自信,而他自己有了一点写作上的自信,全凭不断地学习去熟悉自己所在的这片土地,不断地充实自己。
“很多人把工作和学习理解成一件辛苦的事情,但30岁之后,我发现不断学习是一个很幸福的过程。不断学习,不断地得到,让自己的知识系统更完善,就这样日益丰盈。”阿来透露,他一直在学习,最近在研究苏东坡,读宋史。
(大众新闻记者 师文静)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