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期是一个竞争意识极强的时期。教育者往往会有意识地激发青少年的竞争心理,以推动他们的学业或其他方面的成长。在中国,青少年的竞争主要是学业导向的,他们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同伴之间的成绩竞争。“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这句话道出了青少年的核心焦虑。在无时不在的学业竞争压力下,青少年想“躺平”也很难。客观地讲,同伴学业竞争确实是很多青少年的学习动力所在。中国的青少年进入大学之前,往往准备了比较雄厚的基础知识。这要拜中小学阶段激烈的学业竞争所赐。
理论上说,同辈竞争也能促进青少年人格中抗挫折能力和创造力的发展,但实际情况却并不乐观。在面向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工作中,笔者接触到太多经过了竞争激烈的中学时代,抗挫折能力反而很差、创造力几乎丧失殆尽的例子。更严重的是,笔者和笔者的同事们经常碰到因高考“失利”而变得自卑抑郁的年轻人。有些学生在中小学阶段成绩优异,期待考入名校,认为自己非“985”院校莫属,一旦在考场上发挥不利,进入了“211”或其他类型的院校,就可能产生很强烈的绝望感。

《小欢喜》剧照
假如有人鼓励他们读硕士的时候进入一所名校,他们经常反问:“这能改变我的‘第一学历’吗?”
高考成绩变成了一种终生印记,仿佛它刻在额头上,不是“囚”便是“侯”。这样的学生可能会告诉你:因为他这辈子的“第一学历”都是“211”,将来和那些“985”毕业的高中同学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都会有不配的感觉。
那些如愿以偿跻身名校的,大部分对学问和创造性活动其实没有兴趣,成年后很快就从“比成绩”向“比收入、比职称、比子女”平稳过渡。学业竞争的优胜者获得了进入中产阶级的“通行证”,其功能也就如此而已。
但不论竞争的失败者还是获胜者,似乎都没有把这个竞争仅仅看成竞争本身,或者职业的入场券,它承载了更为宏大的东西,所以才会和人的耻辱感与配得感相联系。

《三十而已》剧照
尽管青少年期的学业竞争推动了学生课业知识的学习,却额外带来了一些效应。有些效应我们可以用“不尽如人意”来形容——例如创造力的平庸——然后付诸一笑。
但有些效应却令人不安。
笔者以往曾经把以分数和应试为导向的教育称为“竞技教育”,并把它跟体育比赛相比较——把求学的过程变成运动生涯,把求学的目的窄化为夺冠拿奖,显然是背离教育的核心目的的。然而,笔者如今意识到这种比较还是相当不准确的。竞技体育给人带来的心理压力与以应试为导向的教育相比还是要小得多,也正常得多。因为“只此一次,再无机会”这样的情况在竞技体育里是不常见的。“即便我硕士考上了清华,我的第一学历还是个‘211’”之类的挫败感恐怕是运动员们体会不到的。也不会有人对运动员说:“虽然你这次拿到了奥运冠军,但你仍然是个没能在第一次大赛就拿奖的二流运动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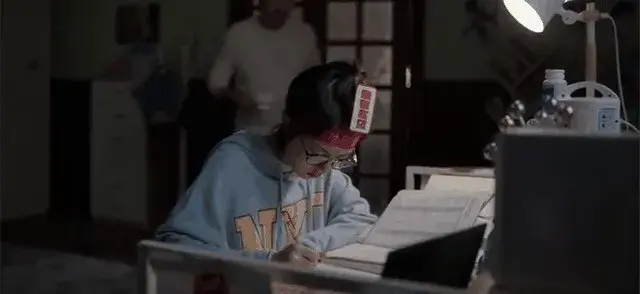
《少年派》剧照
青少年的学业竞争,已经不是“竞技教育”或者“教育的军备竞赛”这样的词能够涵盖的了。高考分数——注意,还不是高考——被赋予了社会分层的意义。其他的考试也如是,例如中考分数往往意味着一个学生能不能进入重点高中,而能否进入重点高中意味着这个学生能否顺利进入重点大学。进入到哪一种大学,关系到将来的求职、升迁、迁徙⋯⋯连香港的“优才计划”,都要给“百强大学”的毕业生加分。甚至中学里每学期每个月的考试,也被赋予了很大的功能——你是不是配待在“重点班”里,这个资格每个月甚至每个星期都要根据分数更新一次。
这类压力运动员没有,可是每个中学生都有。
以应试为导向的教育并不是“竞技教育”,而是一个被广泛认可并不断强化的“学历‘种姓制度’”。通过中考、高考等考试,青少年在心理层面上区分和确认了自己的“学历种姓”。这个身份,是伴随终生的。这个制度虽然没有写到任何一个法条里,却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悄悄地或公开地遵守着。
“学历种姓”对青少年心理层面的影响,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青少年根据成绩和学校形成了清晰明确的歧视链。置身于名校或者优等班,学生往往滋生有如旧时代的贵族所具有的那种优越感。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观念上仿佛又回到了传统社会,要根据某种单一的规则把同龄人准确地等级化,并在这个等级里“心甘情愿”地歧视或者被歧视。年轻人对特权的反感,在应试教育框架下逐渐被磨灭掉。学历“种姓制度”是一种人文退化。
传统社会的特点就是以出身、裙带关系、种族、学历等标签对人进行分层,而不是以人们对社会的实际贡献而给予认可。人类通过文艺复兴、启蒙主义、工业革命等数百年的努力好不容易才带来平等和独立等观念的深入人心。人类之所以走出传统社会,就是因为那样的社会不靠谱,压制人,没创造力,让大多数人没有希望感。那样的社会里的人们想走捷径,搞特权——而不是发展自己的创造能力。以应试为导向的教育不幸落回了这种特权游戏中。想在起点上就把其他人一劳永逸地排除出赛道之外的人类恶习,又变成了合理的活动。
当然,公平地讲,如今这种情况具有世界普遍性,不只是中国一个地方如此。

《小舍得》剧照
笔者不是学业竞争的反对者。学业竞争伤害到青少年的成长,变得弊大于利,那是因为学业竞争蜕化了,它所承载的意义被污染了。这种蜕变和污染最直接的来源就是某些教师和家长。如果教师和家长向学历“种姓制度”低头,甚至他们自己也推波助澜,青少年是没有办法不受影响的——他们只能在庞大的压力和巨大的扭曲面前焦虑恐慌,努力争抢最光鲜最强势的标签。
有一种看法,认为高考指挥棒之类的教育制度安排,是导致教育歧视链、竞技教育等现象的原因。笔者也曾持有这样的观点。但多年来对教育的不断了解,笔者如今更倾向于把学历“种姓制度”看成一种文化现象,从群体心理的角度理解它。学历“种姓制度”起始于人类作为一种灵长类动物对于等级的偏好,这种偏好促使他们去选择标签,并把标签改造成等级。只要一个社会的人文精神疲弱,这种灵长类动物的需求就会占上风。
当1954年教育部推出“重点大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只是意味着国家层面上重点支持几所高校的发展。结果在社会上逐渐就产生了“重点vs非重点”的二极管思维。被教育部重视的大学就被认为优于没有被重视的大学——不论专业如何。考学就要考“重点”大学,不论它们的专业是不是优于“非重点”的大学。结果呢,被重视的大学里所有的专业都会“鸡犬升天”,会因为社会的重视,而产生皮格马利翁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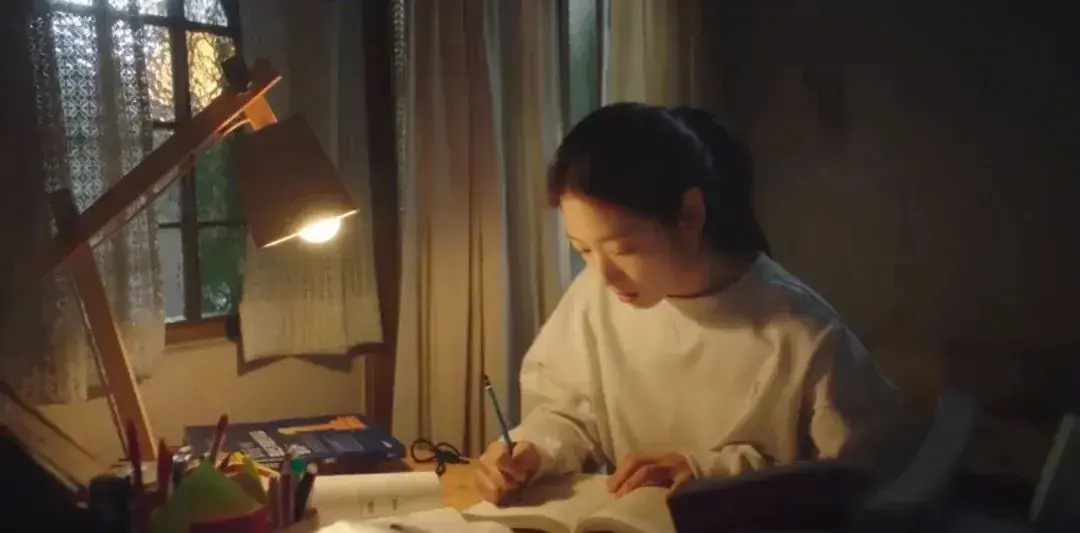
《低谷医生》剧照
追求特权和优越标签的民意像藤子一样,会抓住任何能抓住的东西。重点或非重点、“985”或“211”“双一流”等标签,在最初都不是作为优劣判断的标准而出现的,而是国家战略层面的考虑。但是到了民间,就立刻变成歧视链的依据。甚至从学校里毕业多年的成年人,也会因为母校的这些标签的变化而提升或降低自尊。这种原始的自恋需求本不应该成为主流话语,结果却成了主流话语,这就是形式主义战胜了人文精神的迹象。或者说,也许人文精神在这里从来就没有真正战胜了那种根植于动物性的形式主义。(就像在印度,种姓制度的幽灵从来就没有从那个国家消失。)
人类社会总不免要调动人的生物本能来推动发展。例如市场经济的繁荣,就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人类的完美主义、攀比心、等级意识、虚荣心、自我保护⋯⋯来激发人的购买欲和工作动力。甚至“高大上”的事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其实也在激活知识分子的虚荣心——但它毕竟推动了人类的科学与人文的进步。而诺贝尔奖评委不会告诉人们,没有拿到奖的科学家,是“二流的科学家”或者“不重要的科学家”。然而青少年的老师和家长会认定,没有考上“985”,你就是二流的人。笔者所知的一个中学教师居然偏执地这么对她的学生说:“如果你不好好学习,跳楼都没有人在乎你。”她的言下之意是:一个“优等生”跳楼,会有许多人扼腕叹息。一个“差生”自杀,别人连同情心都不会太多。
学历“种姓制度”大量消耗了年轻人的才智和生命力。我们很容易观察到,“学历辉煌者”容易产生一种强烈的优等感,相应地,是学历不那么辉煌者的劣等感。这种优等感仅仅建立在一两个分数上,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去背书。
一个“211”大学的学生曾告诉笔者:“我站在一个‘985’大学生面前,比站在诺贝尔奖获奖者面前,更容易体验到劣等感。”
这不是很意味深长吗?

《不止不休》剧照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